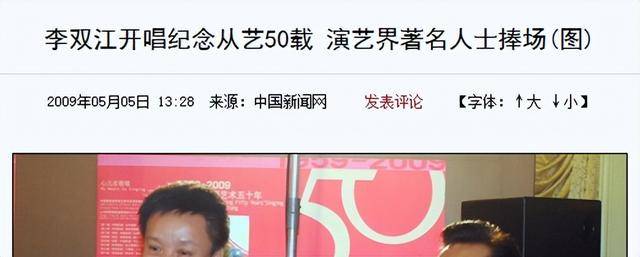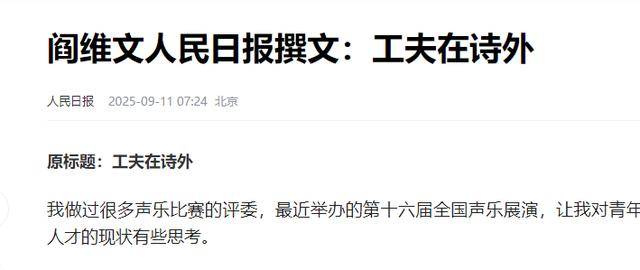原创 人民日报亲自点名,原来阎维文把劲都使在这了,还是李双江看得透
说起阎维文和李双江,这俩军旅歌唱家在咱们这代人心里头,那地位可不一般。
阎维文那首《小白杨》唱了多少年了,还在耳边回荡,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也一样,童年回忆杀。

结果最近人民日报一篇文章,直接把阎维文这些年的日子给扒出来了,原来他没闲着,但路子变了,李双江当年那句话“用心唱歌”还真是一点没错。
讲台和黄土坡
李双江那句“最好的唱法是用心歌唱”,听着简单,却像一道分水岭,把两位军旅歌坛巨匠的晚年人生,划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一个是哈尔滨来的李双江,一个是平遥人阎维文,他们的歌声,曾是几代人共同的记忆。无论是1973年那首销量破三百万、拿下中国首个金唱片奖的《红星照我去战斗》,还是1984年建军节晚会上一鸣惊人的《小白杨》,都早已超越了旋律本身,成为一种精神符号。
李双江把他的理念讲得明明白白:“圆、甜、连、美,用情不用力。”他觉得唱歌不是炫技,是讲故事,得让听众听进去,这个理念,成了他们艺术生涯的共同起点。

可奇怪的是,当阎维文近些年身影逐渐淡出舞台,甚至被人猜测是不是已经退休时,人们才发现,他用一种极为特殊的方式在践行着“用心”二字。而也正是这种践行,最终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让他尝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味。
“用心”这个词,怎么去落地?李双江和阎维文给出了两种答案。

李双江,1963年就从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毕业,根正苗红,1972年调入总政歌舞团,到了1994年,他已经坐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交椅。
他没把这个主任当个虚职,是真刀真枪地干。他搞出了一套叫“红星音乐坛”的教学法,核心就是打破过去那种学生关在琴房里苦练的模式,强调理论必须跟舞台实践结合起来。这套东西在1997年拿了全军教学革新大奖的头名,他主讲的《军旅声乐》课程,后来还被评为国家精品课程。

李双江这是在干嘛?他是在把“用心歌唱”这套感性的理念,变成一套可复制、可传承的学术体系。他用自己的经验和地位,在体制内为后辈们铺路。后来唱出一片天的韩红、雷佳,都曾是他的学生。他的“用心”,是在讲台上,在课堂里,在一代代学生的歌声里传承。

而阎维文的路子,就野多了,他13岁进山西省歌舞团,一开始还是个舞蹈演员。直到1972年,在山西军区战士业余宣传队,他才算正式转行搞声乐。
这种半路出家的经历,或许让他对歌声的源头有更深的执念。当李双江在象牙塔里播撒种子时,阎维文却把目光投向了更远、更荒芜的土地。

从2003年开始,他做出一个让很多人看不懂的决定:减少商业演出,一头扎进了濒危民歌的保护和整理工作里。这不是偶尔下乡采风,而是长达十几年的苦功夫。他背着设备,带着团队,足迹踏遍了19个省份。
在陕西的黄土高坡上,他录下信天游苍凉的调子,在新疆的绿洲旁,他整理濒临失传的木卡姆。在内蒙古的草原上,他记录下马头琴伴唱的悠扬。这些东西,没有商业热度,根本不可能成为流量爆款。

但他还是坚持做了,最后整理出《西域情歌》、《黄土情歌》这些专辑。这哪是歌唱家干的活儿,这分明是个文化苦行僧。他的“用心”,不在聚光灯下,而在田野间,在那些即将消逝的音符里。他选择了一条孤独的文化“逆行”,试图从根上守护“歌”的生命。
里子和面子
阎维文这种“不务正业”的苦差事,一干就是十几年,当很多人以为他渐渐沉寂时,官方媒体却给了他极高的评价。今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他的一篇文章,题为《工夫在诗外》。这篇文章,是他作为第十六届全国声乐展演评委的有感而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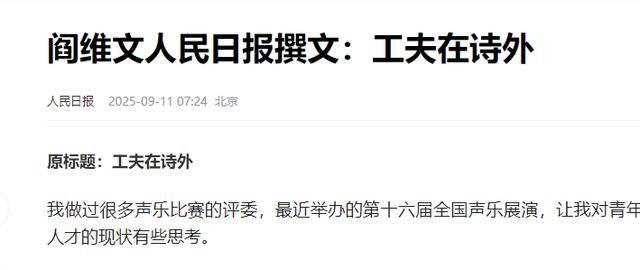
他在文章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现在很多青年歌手的问题:技术基础不牢,选的歌没深度,文化修养跟不上。他还提出,民族声乐要发展,就得融入时尚元素,吸引年轻人。
这番话,结合他十几年如一日的田野采风工作,一下子让他的形象立体起来。《人民日报》的这次“点名”,无异于为他那段“消失”的岁月做了最权威的背书,告诉所有人,阎维文的“工夫”,确实下在了舞台之外,下在了更深厚的文化土壤里。

这一下子,阎维文的“里子”被亮了出来,风评极好,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艺术家不是退休了,而是在做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由官方认证的崇高声誉,却因为之前的一次商业活动,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今年,为了纪念自己从艺55周年,阎维文决定在家乡山西平遥举办一场演唱会,这本是回报桑梓的好事,坏就坏在了门票的发售方式上。想看演唱会?可以,但不能直接买票。你得先去买平遥古城的门票,然后凭门票参与抽奖,抽中了才能入场。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消息一出,网络上瞬间炸了锅。“捆绑消费”、“吃相难看”、“晚节不保”的骂声铺天盖地。很多网友质疑,说好的回报家乡,怎么变成了变相“捞金”?即便官方后来回应说抽奖过程公平,实名核销,也难以平息众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接着,阎维文又被爆出参加了问界M9的车主活动,还在现场对该品牌大加赞美。这一下,他多年来积累的艺术家形象,与商业化、市场化的标签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那个在黄土坡上抢救民歌的文化苦行僧形象,和这个为商业站台的形象,形成了剧烈的冲突。

谁也躲不过时间
其实,无论是选择讲台的李双江,还是奔波于田野的阎维文,他们最终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无法回避的法则——时间。艺术可以永恒,但艺术家的肉身终会老去。
李双江的晚年,更多是从事教学工作,偶尔参加一些活动。但在一次他82岁高龄重返母校中央音乐学院的表演中,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残酷。

舞台上的他,明显气力不足,甚至出现了疑似跑调的情况。这并非丑闻,而是一个歌唱家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曾经的金嗓子,也抵不过岁月的侵蚀。
而阎维文,他的嗓子保养得依旧很好,还能持续在军营里指导年轻歌手,坚持为兵服务,但平遥演唱会的风波,却让他的艺术声誉面临着被商业化反噬的风险。这比嗓子坏掉更麻烦。嗓子的问题是生理的,大家能理解。声誉的问题是选择的,大家会质疑。

他十几年如一日做文化保护,积累了极好的口碑,这是他的“里子”。可一旦与不恰当的商业模式结合,瞬间就会伤害到他的“面子”,甚至让人怀疑他“里子”的纯粹性。
“用心”二字,在年轻时,体现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情感迸发。到了晚年,则更多体现在如何面对生理的衰退、商业的诱惑和舆论的审视。这需要的不只是技巧,更是智慧和定力。

结语
回过头再看,李双江和阎维文的晚年故事,其实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德艺双馨”或者“晚节不保”来粗暴地定义了。他们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艺术家在传承文化与适应时代过程中的真实挣扎与探索。

李双江选择在体制内发光发热,将经验固化为制度,这是他的坚守。阎维文选择走向田野,用脚步丈量文化,这是他的执着。而当阎维文的理想主义撞上现实的商业棱角时所引发的争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复杂的困境:我们既希望艺术家不食人间烟火,又要求他们适应市场规则。

或许,李双江那句“用心歌唱”的真正含义,早已从一种演唱技巧,升华为一种生命态度。那就是在复杂的现实中,如何坚守自己对艺术本真的理解,并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一切可能的结果。他们的探索,无论在别人眼中是成是败,都为后来人留下了无价的思考。
本文信源:人民日报《阎维文人民日报撰文:工夫在诗外》
中国新闻网《李双江开唱纪念从艺50载 演艺界著名人士捧场(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