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穿过镜子的“爱丽丝”
陈冲是20世纪80年代颇具符号意义的演员。大众熟悉陈冲的银幕形象:从影响一代人记忆的“小花”到贝托鲁奇《末代皇帝》中的皇后婉容,对她的家庭背景所知甚少。今年7月,陈冲的第一部非虚构长篇《猫鱼》出版,从上海童年的老房子,到旧金山的家;从祖辈的往事到父母、哥哥几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给读者打开了一个新世界。
陈冲出身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母亲张安中是著名的神经药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培养出了饶毅、晏义平等一批著名学者;父亲陈星荣是放射科方面专家,曾任上海华山医院院长;外婆史伊凡是知名社会活动家,1922年秋入苏州女子师范,与吴健雄等同学,参与过北伐、抗日战争;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太公史蛰夫是一代国学泰斗,曾参加辛亥革命,瞿秋白中学时曾追随他学习篆刻......在《猫鱼》中,四代知识分子的生命史连缀在一起,结成记忆的线索。她用想象力补全了家族历史中自己未曾亲历的画面、场景,投射出一方纸上光影。通过回溯自己的来处、过往(参与过的电影创作、对爱的探索与追寻),她也再次看到自己身上的脆弱与坚韧。基于哀思的记忆和想象激发了她对美的渴望与对艺术的追求。
在成书之前,《收获》文学榜就给了陈冲的文字很高的评价:“(她的写作)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独特又深沉的陈冲,她以克制内敛的笔法向着家族历史征进,踏进如烟的家族往事又不沉溺其中,通过众多日常的生活细节完成了对家人形象的刻写和赋形,从而与历史生活达成了深沉又动人的联系,作品呈现出的沉郁悲悯让人为之动容。”
书名“猫鱼”是陈冲儿时的上海话,菜场出售一种实该漏网的小鱼,用以喂猫,也是她和哥哥陈川(画家)最早在日常生活中体验的“奇迹”。不起眼的猫鱼会因为孩子的恻隐之心暂时被保全,又因为冰冷的空气被冻得僵硬,倒掉后又在温暖的水池里活过来。陈冲相信每个艺术家都有自己童年的“猫鱼”,它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本性中被遗忘或隐藏了的真相”“是我们余生创作最汹涌的源泉”。通过回溯自己的来处和过往,她感到“也许我们每个人,都积累和融汇了所有生命的记忆;也许我们所体验的无常,从来就是永恒。”

《猫鱼》,陈冲 著,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6月。
今年初,我在香港的一场对谈中见到陈冲,她穿黑衬衫配球鞋,显得松弛而神采奕奕。
不可免俗地,聊起她的两大代表作《小花》与《末代皇帝》。忆起前者风靡全国,电影放映员要踩单车,大汗淋漓地一个个乡镇地送胶片,她手势夸张,形容长途跋涉的艰辛;参演后者时阅历尚浅,对导演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推荐的老庄思想与《逍遥游》皆一无所知,她耸耸肩,又露出个无奈神情。
虽然看过几部她的电影,也从父母口中听过,她是让一代人春心荡漾的“小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走出的才女,还有出国引发的争议等。但当陈冲活生生地在我眼前,微卷的短发随着她的动作幅度轻轻摇晃,身为一个对她并没有那么如数家珍的90后,相较种种传奇的经历,我更惊艳于她说故事的魅力,随性、坦率而充满画面感。
文字所呈现的,又比信手拈来的讲述复杂许多。一个多月来,陈冲散文集《猫鱼》,这册六百页的厚书被我辗转带来带去,用她自己形容读金宇澄《繁花》的话,是“几次三番被我从箱子里拿出来,像个护身符那样放在各种陌生的咖啡桌上,离开时又放回箱子”。像虔诚的行为艺术,皆因每个篇章中,她对各种感官的调动,是那么丰富而浓烈。即便已囫囵吞枣通读一遍,偶然翻开,仍像打开潘多拉魔盒,许许多多细节裹挟着情感奔涌而至。
作为一部自传体回忆文集,比起当下流行的非虚构写作技巧,陈冲文如其人,由感性统领的风格,从全书《前记》开头“记忆,好像早晨爱人离别后枕头上柔软的凹印,那是他在你生命里存在过的证据”,就可见一斑。
序言中,编辑金宇澄将她的写作归纳为“是徘徊在‘脑子里全部是戏/完全不记得了’之间的状态,沉浸于只属于她的内心景象里”。透过她的自述,我们得知《猫鱼》之根基,源于疫情时提笔写下的全书第一篇《平江路的老房子》。
金宇澄劝她将其作为提纲,“每一句话可以延伸出十句,每个人可以牵出十件事,里面的空当都是回忆”,可以想象,正如导演之于演员,陈冲对金宇澄交予充分信任,在其依托下发散起舞,将笔触伸向祖辈与父母、爱人与女儿,逐字逐句召唤历史尘烟下早不复在的祖屋,重塑成充满个人色彩,又带着“人去楼空的微微心痛”的记忆宫殿。
家族书写:三代女性
也许女演员的本能就是三言两语搭建出场景,靠画面牵引出层层叠叠的记忆。我想起林青霞在《我魂牵梦萦的台北》中写永康街,再访承载八年青春秘密的老公寓。“重重的铁门栓嘎吱一声移开,一组画面快速闪过我的脑海。妈妈在厨房里为我煮面、楼下古怪的老爷车喇叭声、我飞奔而下、溪边与他一坐数小时、铁门深深地拴上、母亲差点报警。那年我十九,在远赴美国旧金山拍《长情万缕》的前一睌。”

《镜前镜后》,林青霞 著,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11月。
同样以旧宅为载体,陈冲的野心则放眼整个家族。又区别于金宇澄《回望》中,以后设个人私视角遥想父母当年的忧伤咏叹,陈冲叙事经纬之宏大,对标的是王赓武《家园何处是》、齐邦媛《巨流河》等百年心灵史,再穿插实地走访、史料旁证,和借写人写己的剖白,以蒙太奇手法跳跃于过去和当下。导演的职业习惯,是藏在文字背后忽远忽近的镜头,还有洞悉人物的眼睛。
这除了坦诚,更需要节制和勇气。最典型是写她的姥姥(外婆),一位深受学生运动影响,投身革命的反叛世家小姐。登报与父亲断绝关系、只身赴伦敦陪读丈夫,到大后方协助医疗,她数度丢下两个女儿,给她们带来长久阴影。
笔锋一转,陈冲忆起初上大学,由姥姥陪着查字典读英文版《简·爱》,想象书中女主角对广阔天地的向往,曾经也像打动自己一样打动年轻的姥姥。时间线快进,她又谈起女儿13岁患厌食症,原因是分离焦虑,“也许我遗传了姥姥灵魂深处的不安分,无意中总是在伤害我最爱的人,而那份痛心疾首的后悔,也是我必须承担的命运”。

陈冲姥姥、母亲和二姨(从右至左)。
她也以对自己同等的残酷逼视他人。写与母亲通电话,回溯姥姥独自带女儿从上海到重庆。“那些都不是好人,他们占姥姥便宜。我问,怎么占她便宜?母亲犹豫了一下说,她要陪他们睡觉。我哑口无言,完全没想到母亲会跟我这样说”,接下来,她以电影手法虚构姥姥是如何在“占便宜”中九死一生,没有屈辱与不洁,反而显得高傲而狡黠。
再翻两页,踏过惊涛骇浪,来到陈冲留美后返乡探亲一幕,姥姥“请我买一个有波浪的假发套,一个前扣式文胸,一支眉笔和一块羊奶芝士”。刚出国时,陈冲无端卷入舆论风波,唯有姥姥挺身而出,替她写文章辩护奔走,是这位骁勇、果敢,充满坚韧的民国新女性,生前留下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
在写母亲张安中的最后岁月时,陈冲的镜头则蒙上了一层含蓄柔焦。张安中是蜚声国际的药理学家,向媒体官宣去世消息时,她发过一条流传甚广的微博,写母亲“不可腐蚀的纯洁和真”“眼泪这么滚烫,文字这么苍白”,翻阅《猫鱼》对应篇章,却似乎不见相关字眼,仅保留自责段落,“此生第一个爱我的,也是我第一个爱的人在水深火热中受难,我却没有在她身边,人怎么可能从这样的遗憾中走出来?”
在最近与姜文对谈中,陈冲称,写完次日常常大幅删改“虚假、做作或者一种廉价煽情”的内容,这固然是自谦的说法,但也侧面印证只有用内敛的笔,才配得上她的父亲母亲,新中国初代知识分子缄默深沉的厮守。
母亲饱受失忆与癌症煎熬,有时“我叫妈妈,她的眼神从很远的地方收回来”,有时“母亲好像突然想起,她住的地方不是家,她想回家,泪水涌进她困惑的眼睛”。她写在病房里陪母亲唱歌,对她“妹妹啊,妹妹啊”的声声呼唤;写母亲晚年翻来覆去改写早无用武之地的简历,懊恼未完成的失败课题;写一生笃信医学的放射科专家父亲,执拗地一边要不惜代价留住妻子,一边痴狂地进行脑部毛细血管研究;写九旬的他钱包里多了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我想,父亲选了这张照片不是为了记住,而是为了忘却——他想用母亲最美好的样子去冲淡她被病魔摧残的记忆”。

陈冲和母亲在杜邦公司的合影(出版社供图)。
《悲伤是黑镜中的美》,她给母亲圣光中学的同学写信,恳请八九十岁的昔日同窗,拼凑张安中的少女时代;《我们将死于梦醒》,收笔于母亲身故后她回美国前,与父亲无言地吃早饭,“我一个人呆坐在那里,不知怎样才能让他知道我很爱他,我与父亲有太多没说的话”。
读到这里,怀着遣悲怀的心,我翻出我自己的家族故事对照阅读,作者是我母亲,比陈冲小几岁,同为受远大理想感召的80年代文艺青年,她不时写几篇,不作公开发表,仅偶尔传在微信群。
夜深逐个文档点开,却突然觉得以前泛泛看过的内容格外触动 。比如姨婆让她试穿箱底的高跟鞋,“摇摇手叫我不要作声,我穿上感觉长得很高,歪歪扭扭来回走动”;哥哥用玻璃瓶养蟋蟀,“小虫喜欢吃梨子,小指甲盖一块能吃很久,晚上叮铃铃地叫,是那个时代夏天的声音”;写她离世的父母、我的外公外婆,“我常常默默地想,他们相隔12年相聚还会不会认识,我最大的愿望是父亲能自由自在享受生活,母亲一定要学会先爱自己再爱别人”,这些遥远细碎的往事,我母亲在日常生活中提过吗?
大概只有在笔下才能自然流露吧。《十三邀》节目上,许知远提起陈冲有股“经过许多事件身上的重叠感”,她据实以告,“人不是整天都在回忆”。换言之,借用书中她的哥哥陈川,几十年后回顾出国前与姥姥分别的句子,是“后悔自己只说了声再会就离开了,但思索半天也找不出一个恰当的字,我和很多亲人的关系都是这样,也可能我们当年的上海人都是这样,那些感情的话到嘴边就消失了”。
不可思议地,生出了我母亲的书写与陈冲殊途同归的感叹。这种共性与身份、职业和文笔无关,只是那个年代独有的况味。陈冲写过贝托鲁奇给她的启悟,“我们越忠实地表达个人,作品就越具有普世性”,在家族书写中寻觅自我认同,到嘴边消失的话,记忆中闪回的人,交相辉映成历史的棱镜。
光影生涯:乡愁与爱
面对漫长的漂泊,还有事业与爱情撞的南墙,平江路上老房子仍是陈冲的精神原乡,“像护身符一样带来带去”,其脉络之贯穿,在单篇散文结集成书后显得更为清晰。
美国留学,“母亲给我的每一封信里都要加上‘炒菜要小心,油不要溅到眼睛里’,那些年我面对的人生危机母亲无法知道,她只能茫然地担忧,而眼睛被滚油爆瞎这样危险的事,象征一切可能发生在她女儿身上的邪恶”,婚姻失败,一生最孤独失落的一天,“临睡前我想起母亲,她老远老远地正在为我操着心。想起小时候为了手指上的一根小刺,我怎样向她哭喊。今天我就是戴上荆冠也不会忍心让她听见我的呻吟”——成年后,她的身份是妻子或情人,穿过光影流转间的无数角色,陈冲还是平江路170弄的妹妹,在晒台上发呆,需要遮风避雨。
另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情感底色,是陈冲始终带着些自我否定。哪怕美丽和成就已经板上钉钉,她还是“我永远觉得不够好,是伪劣品。或者,这份不安全感是与生俱来的,它一直都在折磨我的同时鞭策我。回头看,我一生的努力都是企图把自己从伪劣品变成真货”。
那根深蒂固、漫长的不自信,也许源于书香名门的光环、才华横溢的哥哥,也许来自年少成名的虚无,曲终人散的反差。正是这份不安全感把年轻的她推向一段段爱情,又以出国为分水岭。
出国前的恋人,就像她演过各种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情节,他们散步、写信,寄送英语书与收音机,月光下称赞她长得像栗园小卷的脸孔,在生机勃勃的集体主义下发乎情止于理。出国后,压抑的一切变得狂野失序,和陌生人骑摩托车去山顶,在医务室和派对的夜晚懵懂而麻木地被性侵,她不掩盖气喘吁吁的情欲,也不讳言支离破碎的伤痕。

电影《红玫瑰白玫瑰》(1994)剧照。
巨细靡遗的挣扎落实在文字间,也一度让我读出些“凡尔赛”的意味。比如她在北京办出国手续留宿在一位编剧家,多年后重遇他的爱人,被告知他们已离婚,丈夫当年不可救药爱上了陈冲,周围人都知道,只有她蒙在鼓里;比如她需要绿卡,遂打电话给三面之缘的N问能否结婚,对方立即应允,表白“你不知道自己有多好”——但另边厢,回看被求婚的当天,她仍由衷地觉得“那么不堪”,“他身上的某种悲剧元素跟我同病相怜,也许我下意识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家,也许我觉得自己已被损坏,不值得有更好的婚姻”。需要承认的是,这种割裂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大概情感泛滥是女演员的充分必要条件,自鄙与自恋是构成戏剧张力的一体之两面。
她自白,“我曾经以为,我的青春被毫无意义的儿女情长燃烧掉了,但也许正是那些灰烬的记忆铸就了我,并仍然铸就着我”。陈冲最经典的两个女主角都与婚姻密不可分,她与她塑造的人物,恰好都处在平行世界的并轨人生。
按照我的私心排序,首先是澳大利亚与新加坡合拍、导演托尼艾尼斯(Tony Ayres)根据其母郭淑华生平改编的电影《意(The Home Song Stories)》。陈冲饰演郭淑华的化身玫瑰,从上海的妾室到香港夜总会舞女,带孩子远渡重洋,与各种男人周旋得头破血流,在与儿女无尽的怨怼后悬梁自尽,结束无所依靠又矛盾重重的一生。玫瑰集她最擅长的破碎、沧桑、情欲与压抑之大成,堪称将婉容与文秀合二为一,她也借此击败凭《色戒》大热的汤唯,《红玫瑰与白玫瑰》后二封金马影后。

电影《意》(2007)剧照。
在《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中,她引用大量在澳洲拍摄《意》时写给丈夫彼得和女儿的信。担心坐飞机失事,担心女儿不接她电话,为家庭聚会歇斯底里,反复梦见彼得离开。患得患失的挤逼下,生活的脆弱与玫瑰的脆弱如宿命相遇。而在彼得的一次次宽慰后,她尝试用自己从洛杉矶飞去旧金山与丈夫初见,那种一见如故、近似血缘的亲切来理解玫瑰,“我认识到,戏中玫瑰的一切行为都怀有强烈的乡愁——心中那个永远失去了的家”。
“我在银幕上扮演过不少女性的角色,但玫瑰是我唯一如此疼惜和捍卫的一个。这个离乡背井渴望归宿的女人,这个被自己的天性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女人”,陈冲写玫瑰,正如写她自己。
后来,导演对她说,尽管成年后大部分时间都在恨母亲,但因为她的表演他爱上了玫瑰,“成为了一条找回母亲郭淑华的途径”——相信这句话超越任何嘉奖,是对演员的最高赞许。而假若将写作视为文本意义的电影,这篇文章则比《意》本身,拥有更隽永动人的余韵。
拍摄《末代皇帝》期间,她与N的第一段婚姻正濒临崩溃。《靠月光寻路》中她写,“贝托鲁奇感觉到我潜意识里的这份伤心和脆弱,他只需为我挖开一条渠道,让它自然流淌出来”,婉容吃花的那场戏,导演对她使用的字眼“塞”和“嚼”,不是“放”或“吃”,粗暴的动词激发了她的疯狂和绝望,而诠释角色则成为宣泄的闸口。

电影《末代皇帝》(1987)剧照。
与婉容溥仪之爱恨并行的,是她与N不可告人的争吵与流血,扭打与求医。她游离到身体之外看这个孤独的女人,紫禁城里雕梁画栋的龙柱,“就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里的那只兔子,把观众带进爱丽丝的兔子洞”,也让她掉落日常之外的另一种人生——对创作者而言,一趟趟的“另一种人生”体验亦反向为生活注入血肉,熔铸成他们的灵魂。
我想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谈论写作的《与死者协商》中,同样引用过“爱丽丝漫游”隐喻:故事开始时,爱丽丝在镜子的这一边,可称为人生的一边,而反爱丽丝,也就是她的倒影,与她左右颠倒的化身,则是在艺术的那一边。但爱丽丝没有打破镜子,弃艺术取坚实明亮的人生面,却反其道而行之,穿过镜子,“真的”爱丽丝没有摧毁化身,而是与之结合,与那个想象的、梦幻的,不存在的爱丽丝结合,当爱丽丝的人生这一面回到清醒世界,也带回了镜中世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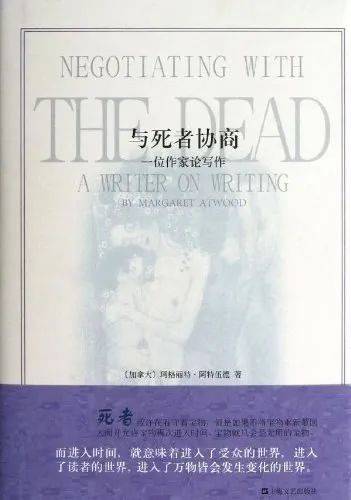
《与死者协商:一个作家论写作》,[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著,王莉娜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
新书上市后,陈冲多次解释过《猫鱼》的含义。如今已被猫粮取代的漏网小鱼,用来喂猫,菜场相当便宜,把它养在大碗,天寒结冰只能倒入马桶,傍晚冰化了,小鱼又活了过来。
除了代表往事不可追,让成长遗迹在笔下复生的愿景。我想,“猫鱼”的另一重意涵,正是冻结与融化的过程,对应爱丽丝对镜子的走入与走出,在过去中寻找未来,陈冲,就是我们时代的爱丽丝。
撰文/一把青
编辑/荷花
校对/卢茜
